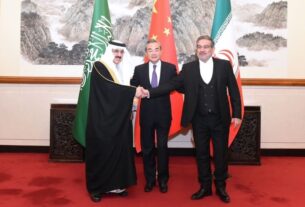帶著愛實現學術的夢想 讓台灣從技術接收者轉變為創造者
許益超教授「以母親為名的學術之路」修補沒說完的親情,他用科學、教育與愛,守住那份聲音的溫度。在世界的舞台上,他讓台灣被聽見;在日常生活中,他讓笑聲繼續發生。
文.邱文通 圖‧許益超提供
馬偕醫學大學聽語學系系主任許益超總說,童年的自己是個安靜的小孩。那不是膽怯,而是一種安靜地與世界對話的能力。他喜歡聽窗外的風、鄰居碗盤碰撞聲、媽媽切菜的節奏,那些聲音,彷彿在說「媽媽在家,一切安好」。
直到讀大學,母親罹癌,他每天傍晚到公共電話亭排隊,只為打一通電話回家,那是母子倆最深的牽繫。然而有一天,母親在電話裡說:「我……聽不太清楚你在說什麼了!」那一刻,如一把剪刀,割斷了兩人之間的連結。他才明白,聲音不是學術名詞,而是一條情感的線,一旦斷了,有些話,再也說不出口。這份痛,種下他一生的志業──讓人重新「聽見」。
學術之路 以母親為名
他走進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的原因很簡單:「我想看看,中醫藥能不能讓像我媽媽那樣的病人,少一點痛。」他帶著愛,走進實驗室,一次次觀察草藥對癌細胞的作用,一步步實現學術的夢想。
但後來,他意識到中醫若要走向世界,必須有一套能被理解的語言──分子生物、幹細胞、動物實驗。他申請進入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幹細胞中心,開始深入神經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。他說:「我進科學,是因為改變不了結局,卻希望未來有人不再那麼痛苦。」他的研究,不只是為了治癒,更是為了修補那段沒說完的親情。他把這條路命名為:「以母親為名的學術之路」。
耳朵,是再生醫學裡極少人關注的領域。但他偏偏選了這條最難走的路。因為「難」才值得,因為它太被忽略。他說:「如果大家都在等,那我來當第一個說『我來了』的人。」
真正促使他下定決心的,是那通中斷的電話。多年後,當他研究纖毛轉錄因子時,意外發現它與聽覺細胞的分化有關,他驚訝地說:「那一刻,好像宇宙偷偷告訴我,你該回到原點了。」
進入馬偕醫學院後,他發現這裡正好擁有最完整的聽覺研究團隊。他說自己就像一根火柴,掉進了火堆,點燃了一整座火種庫。對他而言,耳朵不只是聽覺器官,而是一道門、一道光,一條通往人心深處的路。他希望透過科學,讓那些沒被聽見的愛、壓抑的情感,有一天能再次被世界聽見。
他分享一位天生失聰的十1歲男孩,因 OTOF 基因突變從未聽過聲音,參加了全球首例基因治療。治療後,某日清晨,母親輕喚了他的名字,男孩轉頭、認出、微笑。這不僅僅是科學的數據,而是人與人的連結重新被打開的奇蹟。他說:「我們做的是讓人重新有機會彼此靠近。」他相信,真正的科研價值,不單單在於發表論文,而是讓沉默的母親能再聽見孩子的聲音,讓晚年的夫妻還能說一聲「我愛你」。

教育是讓學生相信自己能發光
他帶著學生走進哈佛醫學院附設麻省眼耳醫院的那天,有學生說:「老師,我從來沒想過,自己能站在這裡。」他回:「你們值得。」那不只是一場學術見習,而是一種眼界與自信的開啟。他說:「教育不是傳授知識,而是讓學生相信自己有重量、有未來。」
對他而言,學生不是他的延伸,而是他真正的成就。他想搭一座橋,讓下一代走得比他更遠,看到更大的世界。二○二五年五月,許教授舉辦第一屆台灣內耳治療國際研討會,主題為「保健、修復、再生、重建」。這不只是醫學對話,更是台灣向世界發聲的起點。他說:「我們不只是追趕世界,而是主動告訴世界──台灣,有能力定義未來的聽覺醫學。」
他期待這場會議不只展現台灣的科研實力,也能激起更多年輕人的熱情。「當世界未來再提起這四個詞,會不會想到台灣?」他語氣平靜卻堅定。這場會議,是他點燃的火,也是台灣從技術接收者轉變為創造者的開始。
實驗室裡,他是研究幹細胞的專家;在會議上,他是推動醫學藍圖的講者。但回到家,他是孩子眼中的爸爸。當壓力來時,他穿上跑鞋,一個人聽著自己的呼吸與腳步,提醒自己:「當你感到疲憊,別忘了你為什麼出發。」他相信,聲音裡藏著情感、記憶與人心。而他這一生的使命,就是讓愛,不再沉默。(取材自《醫學有故事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