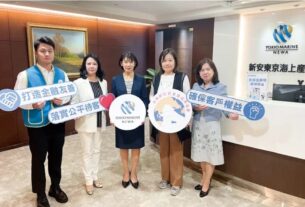文.李振麟
歷經疫情與貿易戰衝突,多年來在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形態下,所建立的全球化供應鏈體制,隨著中美貿易衝突、地緣政治紛擾,最終在保護主義崛起的關稅制度下,走向瓦解一途。
疫情傳染病蔓延,帶給全球公共衛生環境危機,因此各國經濟體不得不採以「區域隔離」或「邊境封鎖」方式來應對。如此一來,也埋下長年依賴全球分工合作的產業鏈,出現許多難以彌補的斷層現象,直到美國川普總統的關稅制度,最終破壞並瓦解多年以來所辛苦建立的全球分工合作產業鏈體系。
新興經濟體也同步遭受到資本市場衰退,帶來許多無法預期的經貿挑戰,如韓國、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國家產業,因為疫情封港與經濟危機影響下,產業投資遞減與關廠外移現象比比皆是,貧富差距在這兩年也不斷地失序擴大,最終中產階級逐漸萎縮,經濟也陷於低迷不振。中美貿易戰下,反全球化熱潮波濤洶湧,保護主義聲勢高漲,關廠潮隨之而起,對於全球產業鏈的衝擊影響,更是令人難以評估,長期以來所依賴的分工合作,也逐漸出現逆襲瓦解之路,無論是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益都面臨極大傷害,為全球化體系帶來嚴峻影響。
「創新技術」與「營運資本」 重塑主導地位
在中美經貿衝突惡化下,「逆全球化」運作,逐漸成為一個新的潮流趨勢。今日高科技或傳統產業,在遭受無情破壞後,業者們不僅失去長期以來的分工合作夥伴,無論是上游的材料資源與下游的消費者族群,都出現難以挽回的結構性破壞,即使不斷地尋找其他供應商,原來的生產成本也都很難再維持現狀。
當商品的成本結構改變後,市場銷售價格也面臨新挑戰,因此需要更長時間來進行調整修正,此時企業自身的營運資金多寡,成為壓倒經營的最後一塊石頭。近幾年來,各國製造業開始思索將部分海外生產線轉回本土,逐漸帶動「再工業化」時代來臨,然而美國川普政權的關稅政策,點燃了這樣思緒。一個擁有廣大內需消費市場與製造業規模的國家,在關稅政策推動下,帶動保守主義崛起,全球各地皆面臨高關稅侵襲而無一倖免,因此去全球化的工業鏈型態逐漸興起。
去全球化的工業型態,不僅誘發創新研發的相關技術受到重視,也為本土製造業帶來新的實體經營與勞工就業機會,在這樣的產業模式下,「創新研發技術」、「降低營運成本」與「經營風險掌控」成為重新塑造事業體營運的基本要素,以本土製造業為起點,進而在全球詭譎多變的經貿環境中,找回最有利的永續發展條件,重新拾回全球產業的主導地位。
要達到「再工業化」條件,除了「營運資本」外,本土「創新技術」的研發能量,將是影響製造業回春的關鍵力量,此時此刻,產、官、學三方面的合作極為重要。如今「AI人工智慧」、「生產自動化」與「大數據運算」,將可望取代傳統經營思維,進而開發與提升自家品牌進入國際市場。在注入創新研發的人工智慧功能下,可將傳統商品轉換成為多功能應用品牌升級,以及自動化生產設備輔助下,減少生產線的勞力與運輸成本支出,在政府部門的獎勵補助扶持下,逐漸勾起製造業回流的意願。
在「逆全球化工業」趨勢發展下,未來的產業鏈將越來越區域性與本土性,透過資本與創新研發技術來提升產品功能,進而將網路系統連結起來,以進行全球性行銷,如中國大陸為避免美國的關稅制裁,將生產線移轉至東南亞國家,再透過資本與網路運作來進行對外商品行銷。
「逆全球化」風潮興起 跨國企業逐漸式微
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政策來保護本國商業利益,跨國企業在此趨勢下的海外經營風險也增加中,近年來,受到中美貿易戰、區域性政策衝突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影響下,許多台灣製造業者,採以「近岸外包」(Nearshoring)策略,將生產線外移至墨西哥,期盼取得相對低廉的人力勞工與土地成本,同時也藉由美墨加協定(USMCA)條款中的關稅優惠,將產品直接從墨西哥輸往美國市場。然而,在美國川普政權開始對墨西哥產業提高關稅,尤其是「汽車零組件」與「鋼鋁產品」等敏感性產業時,也造成所有已轉移至墨西哥的台灣廠商措手不及,不僅造成營運成本增加,市場競爭力也因此受到影響。
尤其是美國的商品進口關稅上調後,原本所預期的低廉成本以及貿易便捷優勢都瞬間被打破,除了墨西哥當地的法規治安與人力成本問題浮現,原本所預估的利潤也因此遞減,還可能面臨消費者轉單風險,台灣企業在墨西哥產業上的環境應變充滿著荊棘又難掌握。如此情況也反映出唯有「逆全球化」政策,將可避免地緣政治風險、經貿政策變動,如今國際市場環境,充滿著許多挑戰性與不可預知性。